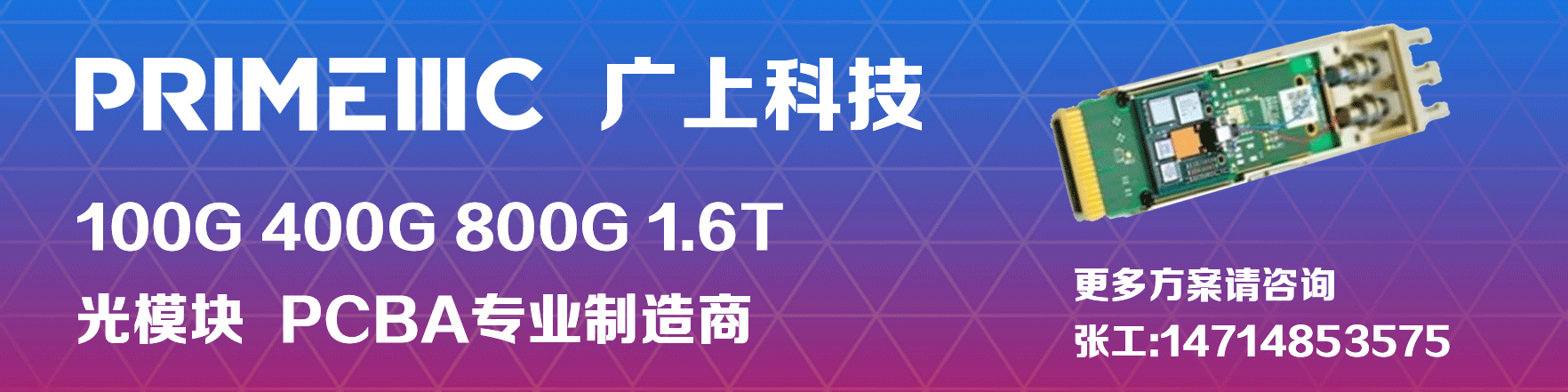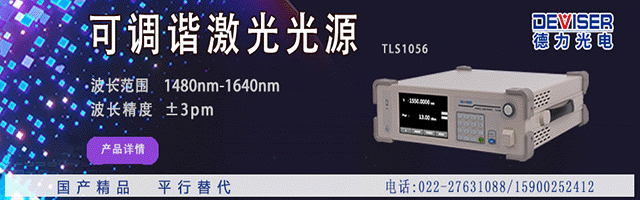侯為貴:一個(gè)老派知識(shí)分子的三十年轉(zhuǎn)型與穿越
訊石光通訊網(wǎng)
2008/12/30 10:03:59
再跌宕的故事到侯為貴口中,都變?yōu)橐晦淝逅?mdash;—這位清瘦的66歲老人,至今依舊保持驚人的老派工程師的本色:目光溫和、言語平實(shí)、內(nèi)向甚至有些靦腆。常年一件普通夾克,拉鏈拉得很上,只露出一點(diǎn)襯衣領(lǐng)子。
但是,他是有鋒芒的,隱藏在他的回答問題時(shí)不粉飾,不躲閃,不掂量里。
比如,他對(duì)當(dāng)年航天系企業(yè)主流“技術(shù)主義”的批判和否認(rèn);
比如,他滿可以逮住CDMA和TD的話題突顯一下中興幾乎“精準(zhǔn)”的預(yù)見力,但他只簡(jiǎn)單地把其歸結(jié)為樸實(shí)的市場(chǎng)邏輯;
再比如,他對(duì)新洋務(wù)派主導(dǎo)中國(guó)對(duì)美金融資產(chǎn)投資的拷問,以及相形之下實(shí)業(yè)領(lǐng)域的被忽略,所表示的不解和微微的憤怒。
教師,技術(shù)員,工程師,經(jīng)理人,及至一家跨國(guó)公司的掌舵者——侯為貴的三十年轉(zhuǎn)型與穿越,在固守淡泊本色的同時(shí),卻擺脫了大多數(shù)老派知識(shí)分子、以及大多數(shù)早期成就的國(guó)有企業(yè)所最終難以逃脫的宿命:
骨子里熱愛實(shí)驗(yàn)室,他招攬一批“學(xué)院派”學(xué)者、教師共同創(chuàng)業(yè),但他的企業(yè)順利地克服了技術(shù)派的偏執(zhí)和盲從;淡漠名利,不事張揚(yáng),但是他深知產(chǎn)權(quán)關(guān)系是激活企業(yè)發(fā)展的要害,率領(lǐng)一批工程師率先走上了“去國(guó)有化”的道路,并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批科技致富的受益者。
與此同時(shí),他先后到過70多個(gè)國(guó)家,并把產(chǎn)品成功銷往世界130多個(gè)國(guó)家和地區(qū),他推動(dòng)了一個(gè)中國(guó)科技公司的全球化,產(chǎn)品所到之處亦見證了中國(guó)外交關(guān)系的三十年變遷……所有的這些,都足以證明,為什么我們會(huì)選擇侯為貴和他創(chuàng)辦的這家公司作為本組改革開放“南方的啟示”高端系列訪談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
不僅如此,中興通訊的成長(zhǎng)還驗(yàn)證了中國(guó)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參與全球競(jìng)爭(zhēng)過程中,每前進(jìn)一步所付出的艱難與博弈——我們看到中興通訊、華為兩家真正意義上的跨國(guó)公司崛起背后,仍顯蒼涼的國(guó)家背影:改革開放以來中國(guó)在中低端產(chǎn)業(yè)鏈上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力已經(jīng)步入全球最強(qiáng)行列,但是在金融、科技領(lǐng)域還處于相當(dāng)?shù)偷乃疁?zhǔn)。本輪“次貸危機(jī)”讓我們意識(shí)到,此種“國(guó)際化“不但利潤(rùn)低下,也難以持久。
改革開放之后,我們?cè)诮^大多數(shù)商業(yè)市場(chǎng)領(lǐng)域幾乎沒有一項(xiàng)重大的高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,一方面,很多科技成果僅僅停留在實(shí)驗(yàn)室,沒有實(shí)現(xiàn)“技術(shù)產(chǎn)品化”,更不用說“產(chǎn)品產(chǎn)業(yè)化”和成功市場(chǎng)化;另一方面,中國(guó)絕大多數(shù)企業(yè)難以像中興那樣持續(xù)進(jìn)行數(shù)以億計(jì)、歷時(shí)數(shù)年乃至十?dāng)?shù)年沒有利潤(rùn)的投入,無力與規(guī)模百倍于自己并具有先發(fā)優(yōu)勢(shì)的跨國(guó)企業(yè)進(jìn)行競(jìng)爭(zhēng)。遍覽IT通信、醫(yī)藥、自動(dòng)化等最能體現(xiàn)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的領(lǐng)域,中國(guó)像中興這樣成功的高技術(shù)企業(yè)寥寥。
改革開放所奉行的一條國(guó)家哲學(xué)與商業(yè)邏輯——市場(chǎng)自由競(jìng)爭(zhēng)必然會(huì)產(chǎn)生最強(qiáng)者——在全球化已過半程的今天正在遭受越發(fā)嚴(yán)峻的挑戰(zhàn),西方國(guó)家作為先發(fā)者的強(qiáng)勢(shì)力量滲透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科技、金融等諸多領(lǐng)域,為作為后來者的發(fā)展中國(guó)家制造巨大的超越障礙——這樣的矛盾,是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路徑依賴的體現(xiàn),也是創(chuàng)新成本與中國(guó)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能力之間的根本矛盾,是發(fā)展中國(guó)家的創(chuàng)新悖論。
中國(guó)能否在高端制造業(yè)、高端服務(wù)領(lǐng)域再持續(xù)產(chǎn)生出更多的中興、華為——這樣的追問將縈繞著我們的下一個(gè)30年。
連侯為貴也慎言,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,再出現(xiàn)中興、華為這樣的企業(yè)機(jī)率已越發(fā)迷茫。這并不難理解,就算在制度完善、資本充足的美國(guó),也難以再造一個(gè)思科、IBM、微軟或者強(qiáng)生制藥。這是全球化博弈形成的事實(shí)性霸權(quán)版圖,專利、制度、標(biāo)準(zhǔn)都是先行者的“合法”工具。
這個(gè)矛盾放在中國(guó)未來發(fā)展的長(zhǎng)期戰(zhàn)略視野里就會(huì)折射出更大的矛盾?;仡欉^去30年以來的中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在每個(gè)階段所獲得的動(dòng)力:1980年代解放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力和發(fā)展輕工業(yè),本質(zhì)是解放低級(jí)生產(chǎn)力;90年代初期開始的市場(chǎng)化、城市化、重工業(yè)化,本質(zhì)是通過生產(chǎn)資料投資發(fā)展生產(chǎn)力;2000年以來,資本化、科技化和國(guó)際化是中國(guó)向更高水平發(fā)展的主要?jiǎng)恿Γ?ldquo;科技是第一生產(chǎn)力”,以人才和創(chuàng)新為核心的戰(zhàn)略是中國(guó)未來的必然選擇。
如是,我們采擷自主創(chuàng)新“中興樣本”,為我們探討下一個(gè)30年國(guó)家創(chuàng)新路徑和企業(yè)路徑的融合,尋找一盞明燈。
30年角色轉(zhuǎn)型
“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也是要眼見為實(shí)的”
上世紀(jì)80年代初,侯為貴說服航天系統(tǒng)的領(lǐng)導(dǎo),以“引進(jìn)技術(shù)”的名義來到深圳,1985年創(chuàng)辦中興通訊前身——深圳中興半導(dǎo)體有限公司成立,由航天系統(tǒng)的691廠和運(yùn)興香港電子企業(yè)及另外一家國(guó)有企業(yè)三家聯(lián)合投資組成。
《21世紀(jì)》:1984年創(chuàng)辦中興半導(dǎo)體公司之前,您在航天工業(yè)部旗下的691廠工作。從西安到深圳、從國(guó)有企業(yè)到創(chuàng)業(yè),什么是實(shí)現(xiàn)這一轉(zhuǎn)變的歷史契機(jī)?
侯為貴:航天部當(dāng)時(shí)在全國(guó)都有企業(yè),但性質(zhì)都是國(guó)企。到深圳后創(chuàng)辦企業(yè)這個(gè)事有點(diǎn)偶然。我最早在航天部設(shè)在西安的691廠,這個(gè)企業(yè)早先是一個(gè)中專學(xué)校,我畢業(yè)分配到那做了一名教師。1969年,文化大革命,學(xué)校都停了,轉(zhuǎn)變?yōu)槠髽I(yè)。當(dāng)時(shí)的航天部副部長(zhǎng)錢學(xué)森給我們提一個(gè)要求,要我們做IC(半導(dǎo)體)。當(dāng)時(shí)部里掌握的美國(guó)信息是,美國(guó)剛剛啟動(dòng)IC產(chǎn)業(yè),所以學(xué)校就轉(zhuǎn)型開始做IC,變成一個(gè)工廠。那時(shí)候沒有工程師的說法,我從老師變成了技術(shù)員,后來從技術(shù)員升任技術(shù)科長(zhǎng)。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很亂,但是在它結(jié)束前后我們實(shí)際上已經(jīng)開始引進(jìn)一些國(guó)外的技術(shù),這是在國(guó)內(nèi)最早的。后來我在1981年第一次去了美國(guó),也是負(fù)責(zé)引進(jìn)技術(shù)和設(shè)備。也是因?yàn)楦慵夹g(shù)引進(jìn)的原因,我到了深圳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您還記得第一次到美國(guó)時(shí)的感受嗎?去了哪些地方?
侯為貴:當(dāng)時(shí)到了美國(guó)等于是到了另外一個(gè)星球上,是這種感覺,在國(guó)內(nèi)當(dāng)時(shí)人與人是很封閉的。去的地方不多,主要集中在美國(guó)西北部芝加哥等地方,呆了一個(gè)多月,實(shí)際上我們?nèi)ブ熬鸵呀?jīng)看過大量的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的資料,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時(shí)候,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技術(shù)資料的,技術(shù)資料與市場(chǎng)的關(guān)聯(lián)度也很大,所以我們對(duì)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的理解很早就有了,只是因?yàn)?0年代初的時(shí)候,雖然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的因素已經(jīng)影響到中國(guó),但大多數(shù)人不關(guān)注這些東西,尤其搞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的人不太關(guān)注,我們?cè)谄髽I(yè)里面搞引進(jìn)工作的關(guān)注得多一些。
《21世紀(jì)》:當(dāng)時(shí)還沒有提“有計(jì)劃的商品經(jīng)濟(jì)”吧?在美國(guó)的時(shí)候,有沒有感受到來自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、企業(yè)體制的沖擊?
侯為貴:當(dāng)時(shí)還沒有說計(jì)劃要搞“有計(jì)劃的商品經(jīng)濟(jì)”,那是后來才提的。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也是要眼見為實(shí)的,實(shí)際上從理論上我們很早就知道了,但真正的親眼所見那是那一次。比如他們對(duì)原材料的選擇,怎么樣能夠降低成本?當(dāng)時(shí)對(duì)成本這個(gè)東西考慮不是太多的,特別是航天系的企業(yè),只要能夠上天,成本不計(jì)較,我們做的集成電路廣角電鍍,鍍金都很厚,幾個(gè)微米,美國(guó)人就說,你這樣是不對(duì)的,你這個(gè)錢往地下亂撒,不需要做這么厚的金同樣能保證質(zhì)量——這個(gè)給我印象確實(shí)比較深,人家的企業(yè)是從成本管理的角度出發(fā),我們國(guó)內(nèi)當(dāng)時(shí)對(duì)成本的概念是很淡薄的。
《21世紀(jì)》:1985年,您主導(dǎo)幾家國(guó)有企業(yè)一起創(chuàng)辦“中興半導(dǎo)體”時(shí),深圳是梁湘主導(dǎo)的時(shí)期代,當(dāng)時(shí)還是以貿(mào)易、來料加工、搞基建為主,走私也比較興盛,“合辦企業(yè)”卻是很少見。這些企業(yè)在李灝主政深圳的時(shí)候才興起,中興搞合辦企業(yè)的時(shí)候在李灝時(shí)代之前。
侯為貴:對(duì),比較早,我們建立合辦企業(yè)的時(shí)候還是梁湘時(shí)代,我們都是從國(guó)營(yíng)企業(yè)出來的,辦企業(yè)開始肯定還是想以國(guó)營(yíng)企業(yè)作為大股東,我們只是在里面做管理工作當(dāng)總經(jīng)理,思維方式還是有一定局限性,當(dāng)時(shí)沒有想自己做私營(yíng)企業(yè)。但是當(dāng)時(shí)現(xiàn)實(shí)是國(guó)有性質(zhì)的西安母公司不可能出錢,所以我們?cè)谶@一點(diǎn)上比較明確——不要讓它(國(guó)企)承擔(dān)太大風(fēng)險(xiǎn),沒讓他們出錢,只給我提供了一個(gè)擔(dān)保就行。后來我們把錢一還,它的擔(dān)保就沒有風(fēng)險(xiǎn)了。我們這么做同時(shí)也是想將來它(國(guó)企)不會(huì)干預(yù)太多,給我們爭(zhēng)取多一點(diǎn)自由度。對(duì)國(guó)企來說,不掏錢就沒有責(zé)任和損失。但董事長(zhǎng)還是西安691廠的人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既然西安母公司不出錢,那么創(chuàng)業(yè)的錢怎么來的?
侯為貴:錢是我們自己掙的。因?yàn)樗▏?guó)企)給我做了一點(diǎn)擔(dān)保,有了一點(diǎn)錢,就開始做了一些貿(mào)易加工,玩具、風(fēng)扇、電子琴我們都做過,這個(gè)增長(zhǎng)很快,產(chǎn)生的利潤(rùn)就變成企業(yè)的啟動(dòng)資金了。1985年也向國(guó)防系統(tǒng)內(nèi)部貸過一點(diǎn)款,1987年就全部都還了。
“把市場(chǎng)、客戶放在第一位,還是把政府作用放在第一位,這是核心問題”
業(yè)界都把中興在1993年的那次“國(guó)有民營(yíng)”化改革作為其日后騰飛的起點(diǎn)。那一年,國(guó)有企業(yè)691廠、深圳廣宇工業(yè)(集團(tuán))公司與一家由侯為貴等30多名自然人組成的民營(yíng)企業(yè)“維先通”實(shí)施了第一次重組,共同投資創(chuàng)建了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(shè)備有限公司,兩家國(guó)有企業(yè)控股51%,民營(yíng)企業(yè)“維先通”占股份49%,由“維先通”承擔(dān)經(jīng)營(yíng)責(zé)任,在國(guó)內(nèi)首創(chuàng)了“國(guó)有控股,授權(quán)(民營(yíng))經(jīng)營(yíng)”的“混合經(jīng)濟(jì)”模式。明確公司人、財(cái)、物的經(jīng)營(yíng)權(quán)全部歸經(jīng)營(yíng)者;經(jīng)營(yíng)者須保證國(guó)有資產(chǎn)按一定比例增值。若經(jīng)營(yíng)不善,經(jīng)營(yíng)者須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權(quán)益抵押補(bǔ)償;若超額完成指標(biāo),則獲得獎(jiǎng)勵(lì)。補(bǔ)償和獎(jiǎng)勵(lì)幅度均為不足和超額部分的20%——可以說,沒有這次重要的產(chǎn)權(quán)改革,中興很有可能與已經(jīng)消逝的國(guó)有企業(yè)“巨龍”一樣,成為歷史的塵埃。
工商資料顯示,維先通股東名單上,至今仍是當(dāng)年跟著侯為貴創(chuàng)業(yè)的33名自然人,“維先通”目前是中興通訊(000063,SZ)的實(shí)際第一大股東。
《21世紀(jì)》:1993年成立的“中興新”在國(guó)內(nèi)是首家建立“國(guó)有民營(yíng)”產(chǎn)權(quán)關(guān)系的企業(yè),這是不是多少受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影響?
侯為貴:是的,有關(guān)系。這時(shí)候思想就更加開放一點(diǎn)。我那時(shí)候就想,這樣搞下去也沒有什么發(fā)展,一定要轉(zhuǎn)變一下產(chǎn)權(quán)關(guān)系,不搞中外合資了,必須自主發(fā)展。所以我們從1992年就改制,由我們這些骨干用自己錢投資成立了一家民營(yíng)企業(yè)“維先通”,然后1993年再跟航天系的兩家企業(yè)重新合資,成立了“中興新”,辦公室從八卦嶺搬到了蓮塘。
《21世紀(jì)》:“維先通”一開始就是一家完全自然人持股的公司嗎?國(guó)有企業(yè)依舊占51%控股權(quán),是否還是會(huì)影響到企業(yè)未來的決策和經(jīng)營(yíng)?
侯為貴:是自然人,由當(dāng)時(shí)公司的骨干共同持有的公司。國(guó)有企業(yè)占大股不是我們的意愿,是北京部委方面要求占51%,我們當(dāng)時(shí)也沒有太多想法。但是因?yàn)檫@么多年大股東并沒有出資,都是我們用每年利潤(rùn)給他填進(jìn)來的,從1985年開始到1993年的八年間利潤(rùn)分紅之外,有一部分就留下來作為國(guó)企的股份錢。
經(jīng)營(yíng)理念上股東之間還是有差距的,航天系是崇尚技術(shù)的,但是他們對(duì)市場(chǎng)的敏感度比較低,我們雖然也很重視技術(shù),但在深圳形成了很強(qiáng)的市場(chǎng)的意識(shí),我們認(rèn)為,市場(chǎng)是第一要素,技術(shù)只有跟市場(chǎng)結(jié)合才有可能逐步地發(fā)展,才能做大規(guī)模。純粹的技術(shù)主義,除非是國(guó)家投入,像航天項(xiàng)目,否則難以為繼。雖然意見不統(tǒng)一,但是因?yàn)橐婚_始我們就沒讓他們(國(guó)有股東)掏過錢,他也就不好過多干預(yù)。當(dāng)然也先后派了好多次董事長(zhǎng),也有認(rèn)為我是大股東我要干預(yù)的,但是我們還是堅(jiān)持市場(chǎng)導(dǎo)向,因?yàn)槲沂强偨?jīng)理,要吃飯,要生存,必須要在市場(chǎng)上投入更多精力。
《21世紀(jì)》:1993年這一次體制上的變革是中興發(fā)展是你們非常重要的一個(gè)轉(zhuǎn)折?這次改制后解決了公司未來發(fā)展哪些關(guān)鍵性問題,比如說,公司未來要賺什么錢,快錢還是技術(shù)的錢?從中興起家看,做過很多產(chǎn)品,為什么今天的中興發(fā)展成為一家通訊設(shè)備公司,而不是一家生產(chǎn)玩具、或電扇的公司?
侯為貴:做中興半導(dǎo)體公司的時(shí)候,股東之間的矛盾多,往前發(fā)展很難,后來轉(zhuǎn)型改制后產(chǎn)權(quán)關(guān)系理順了才推動(dòng)了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在公司發(fā)展上,我們很早就開始和國(guó)家郵電部下面的一些單位合作研制電話機(jī)和通信產(chǎn)品,是1986年,一開始做電話機(jī)和68門的小型用戶交換機(jī)。雖然我們也做過很多來料加工的活,但我們的技術(shù)背景是做半導(dǎo)體的,半導(dǎo)體是一個(gè)高技術(shù),通信產(chǎn)品和集成電路關(guān)系比較大,這樣幫助我們對(duì)電話機(jī)和通訊產(chǎn)業(yè)有更好的理解。這個(gè)行業(yè)技術(shù)含量高,而且我們也覺得通訊未來的需求量比較大,所以我們從市場(chǎng)和技術(shù)兩個(gè)角度來選擇的。電扇、玩具我們認(rèn)為技術(shù)非常簡(jiǎn)單,我們是從航電出來的,這些簡(jiǎn)單的產(chǎn)品我們也看不上,來料加工,我們不用投多少精力,弄幾個(gè)人組織一下就行了,我們的精力集中在通訊產(chǎn)品上。
“巨大中華”浪淘沙
大浪淘沙——20世紀(jì)80年代,全國(guó)上下,從農(nóng)話到國(guó)家骨干電話網(wǎng)用的全是國(guó)外進(jìn)口的設(shè)備,行業(yè)內(nèi)流傳著“七國(guó)八制”的說法,在“巨大中華”等本土公司崛起后,局面日漸改變。令人扼腕的是,占據(jù)資源最多,獲得政府支持最大的“巨龍”在短暫的輝煌后退出歷史舞臺(tái),國(guó)有背景的大唐勢(shì)頭亦遠(yuǎn)遠(yuǎn)弱于南方的“中華”——體制優(yōu)劣由此可見。
《21世紀(jì)》:倒退十幾年來看,當(dāng)時(shí)巨龍和大唐在政府支持以及運(yùn)營(yíng)商資源上,都優(yōu)于中興和華為,但是后來他們卻很快衰落了。“巨大中華”的發(fā)展軌跡、發(fā)展速度、規(guī)模與公司體制和治理結(jié)構(gòu)有一個(gè)正相關(guān)的關(guān)系?
侯為貴:實(shí)際上我認(rèn)為大唐和巨龍,他們堅(jiān)持的是技術(shù)第一,政府第二。兩家的出身一個(gè)是郵科院,一個(gè)是軍工口的研究所。公司內(nèi)部都是一幫老工程師、研究員,相對(duì)純粹地是搞研究出身的,所以容易堅(jiān)持技術(shù)第一,所以一開始技術(shù)走得還是比較快的;但體制上是100%政府控制,有什么事就找政府,包括通過政府渠道拿到訂單,所以市場(chǎng)能力、市場(chǎng)服務(wù)都比較弱。其實(shí)巨龍做得比我們?cè)?,早期的市?chǎng)份額也比較高,但是它在市場(chǎng)上一旦有問題就通過政府施壓來解決,同時(shí)服務(wù)和售后跟不上,客戶慢慢的就對(duì)它也就失去了信心。這兩家都有這樣的問題,其實(shí)他們有過很好的機(jī)會(huì)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您認(rèn)為這跟體制有關(guān)系嗎?
侯為貴:應(yīng)該有一些原因。另外的關(guān)鍵,是經(jīng)營(yíng)者的指導(dǎo)思想有沒有轉(zhuǎn)型——你究竟是把市場(chǎng)、客戶放在第一位,還是把政府作用放在第一位,這是核心問題。
《21世紀(jì)》:除了“巨大中華”,按說90年代初中國(guó)電信市場(chǎng)處于噴發(fā)期時(shí),當(dāng)時(shí)南方乘勢(shì)而起的企業(yè)也有不少“市場(chǎng)導(dǎo)向”的,他們?yōu)槭裁春髞硪驳瓜铝四兀?/font>
侯為貴:是的,當(dāng)時(shí)做用戶交換機(jī)有幾百家企業(yè),數(shù)量非常大,但是有的企業(yè)到后面就不行了,要不就是對(duì)市場(chǎng)的敏感度不夠,要不就是沒有在技術(shù)上持續(xù)投入,各種原因慢慢地就淘汰了。也有很多企業(yè)眼光很短,弄點(diǎn)錢,自己就開始買高級(jí)車,消費(fèi)了。(笑)他們沒有一個(gè)定力往前發(fā)展,有的也是國(guó)有背景的,比如當(dāng)時(shí)的長(zhǎng)虹通訊,開始做交換機(jī)的時(shí)候他們做的市場(chǎng)份額比我們還大,后來也沒有得到發(fā)展,有各種各樣的原因。
“在競(jìng)爭(zhēng)中成長(zhǎng)起來的企業(yè),應(yīng)該說它的體制會(huì)比較好”
《21世紀(jì)》:“巨大中華”崛起前,中國(guó)電信設(shè)備市場(chǎng)上有“七國(guó)八制”的說法,可以說,國(guó)產(chǎn)廠商的出現(xiàn)打破了國(guó)外廠商壟斷中國(guó)市場(chǎng)的局面,能否回顧一下當(dāng)時(shí)情況?
侯為貴:中國(guó)一開始是沒有通訊技術(shù)的,1980年代初日本富士通最早登陸福建,建了個(gè)150合資廠,然后在江蘇等地建了一些廠,后來包括NEC、愛立信、西門子等也都進(jìn)來了,他們統(tǒng)治了中國(guó),所以有“七國(guó)八制”的說法。
外國(guó)人擁有技術(shù)、設(shè)備,開始在中國(guó)做交換機(jī)。中國(guó)人當(dāng)時(shí)是沒有這個(gè)技術(shù)的,有一個(gè)學(xué)習(xí)過程。我們從小交換機(jī)到大交換機(jī)整整用了七八年時(shí)間,因?yàn)閲?guó)外的技術(shù)發(fā)展相對(duì)慢,我們走得快,另外我們的服務(wù)更及時(shí)到位,所以才捕捉到了機(jī)會(huì)。到現(xiàn)在國(guó)外廠商壟斷的局面也沒有完全地解決。這個(gè)過程就是一點(diǎn)點(diǎn)積累的結(jié)果,每一個(gè)小的戰(zhàn)場(chǎng),都要刺刀見紅,然后能拼下去,慢慢地?cái)U(kuò)大我們的地盤。
《21世紀(jì)》:過去30年,日系廠商衰退,中國(guó)廠商的崛起,一起一落間是不是也說明一個(gè)問題:中國(guó)的電信設(shè)備市場(chǎng)一開始就是充分開放充分競(jìng)爭(zhēng)的,所以才煉成了中興、華為這樣有國(guó)際競(jìng)爭(zhēng)力的企業(yè);相反,日本本國(guó)封閉型的政策,雖然初衷是為了扶持本國(guó)企業(yè),反而讓他們失去了競(jìng)爭(zhēng)力?
侯為貴:競(jìng)爭(zhēng)應(yīng)該是一個(gè)要素,在競(jìng)爭(zhēng)中成長(zhǎng)起來的企業(yè),應(yīng)該說它的體制會(huì)比較好。我們?cè)趪?guó)內(nèi)與“七國(guó)八制”打斗了這么多年,到國(guó)外去打斗其實(shí)還是這個(gè)招數(shù),實(shí)際上在國(guó)內(nèi)殘酷競(jìng)爭(zhēng)的這些年增強(qiáng)了企業(yè)的內(nèi)功。同時(shí),還有一個(gè)重要因素,就是技術(shù)成本問題,國(guó)外廠商成本太高,像北電過去有段時(shí)間很紅火,但最近一直在破產(chǎn)邊緣,包括美國(guó)的朗訊與阿爾卡特合并,摩托羅拉也在急劇下降,這些企業(yè)跟日本企業(yè)的國(guó)情都不一樣,但是也在不約而同地走下坡路。所以技術(shù)成本過高也是一個(gè)核心問題。
《21世紀(jì)》:中國(guó)技術(shù)成本優(yōu)勢(shì)意味著什么?
侯為貴:現(xiàn)在的技術(shù)流程變化越來越快,他(國(guó)外廠商)體制上肯定有一些傳統(tǒng)的東西不符合現(xiàn)代技術(shù)的快速發(fā)展。在這個(gè)過程中,技術(shù)人力成本優(yōu)勢(shì)在競(jìng)爭(zhēng)中起到關(guān)鍵性作用?,F(xiàn)在市場(chǎng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大家都困難,包括歐美國(guó)家的運(yùn)營(yíng)商都希望價(jià)格低,競(jìng)爭(zhēng)就會(huì)激烈,最終用戶的價(jià)格都體現(xiàn)在網(wǎng)絡(luò)的總體成本上,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話,最終運(yùn)營(yíng)商優(yōu)勢(shì)還是要下降。所以這個(gè)行業(yè)競(jìng)爭(zhēng)是多角度的,技術(shù)上要先跟得上,這個(gè)行業(yè)發(fā)展特別快,老是在革命,老是在換代,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利用中國(guó)技術(shù)成本的優(yōu)勢(shì)走快一點(diǎn),因?yàn)檫@個(gè)行業(yè)每一次革命都需要重新洗牌,都要變,國(guó)外廠商變化慢,所以我們機(jī)會(huì)就多一點(diǎn)。
偉大的博弈
有人說,中興通訊是精準(zhǔn)地踩著中國(guó)電信市場(chǎng)的每個(gè)鼓點(diǎn)成長(zhǎng)起來的:中國(guó)電信、網(wǎng)通的小靈通,中國(guó)聯(lián)通的CDMA,最近沸反盈天的TD—SCDMA——如果僅僅把這些歸結(jié)為市場(chǎng),或者技術(shù)的勝利,是遠(yuǎn)遠(yuǎn)不夠的。實(shí)際上在每一次運(yùn)營(yíng)商決策、每一種電信制式的選擇的背后,都包含了復(fù)雜而艱苦卓絕的斗爭(zhēng)與搏弈,這其中包括以WCDMA、CDMA2000、WIMAX、TD-SCDMA所代表的各大跨國(guó)企業(yè)利益集團(tuán)之間的競(jìng)逐,還包括大國(guó)之間在高端產(chǎn)業(yè)、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戰(zhàn)役當(dāng)中話語權(quán)的爭(zhēng)奪。
《21世紀(jì)》:倒退20年,您如何判斷移動(dòng)通信市場(chǎng)潛在的歷史機(jī)遇的?比如CDMA,當(dāng)時(shí)聯(lián)通會(huì)不會(huì)上CDMA是一個(gè)復(fù)雜的博弈局面,不僅是企業(yè)之間的博弈,也有國(guó)家之間的博弈,您當(dāng)時(shí)如何判斷CDMA一定會(huì)上的?您當(dāng)時(shí)怎么計(jì)算投入產(chǎn)出比?
侯為貴:市場(chǎng)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戰(zhàn)爭(zhēng)和博弈,不管2G,還是3G。我們作為一個(gè)后進(jìn)者在很多領(lǐng)域都是從后往前趕,以圖將來我們成為主流。移動(dòng)電信市場(chǎng)這個(gè)東西,10年前我們剛起步的時(shí)候,從全球的角度看潛力就非常大。我1999年第一次去印度,那時(shí)候印度才360萬用戶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2億多了,連續(xù)五六年時(shí)間里每年都是翻一番;這個(gè)過程中國(guó)當(dāng)年也經(jīng)歷過來了,CDMA當(dāng)時(shí)中國(guó)沒有一個(gè)明顯的信號(hào)是一定要上,我們做CDMA最早的思路是即使中國(guó)不上,國(guó)外的市場(chǎng)還是很明確的,因?yàn)楫吘故敲绹?guó)標(biāo)準(zhǔn),而且是當(dāng)時(shí)全球兩個(gè)主要標(biāo)準(zhǔn)之一,即便國(guó)內(nèi)不上,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上產(chǎn)品也養(yǎng)得起。
對(duì)CDMA我們實(shí)際上1995年就開始從芯片級(jí)自己都在做研發(fā),那時(shí)候還沒有引進(jìn)高通的東西,雖然市場(chǎng)銷售當(dāng)時(shí)還不太成功,但是鍛煉了一批隊(duì)伍。我們也一直在觀察。有一段時(shí)間,公司內(nèi)部也有分歧認(rèn)為戰(zhàn)線太長(zhǎng)了,是不是把它下掉?后來我們還是堅(jiān)持以比較小的隊(duì)伍延續(xù)發(fā)展,等到市場(chǎng)機(jī)遇爆發(fā)的時(shí)候,技術(shù)也積累得差不多了,這時(shí)候再大規(guī)模地上人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您對(duì)現(xiàn)在發(fā)的三個(gè)3G牌照安排怎么看?
侯為貴:首先是3G的進(jìn)度,其實(shí)歐洲、日本早在十年前(1998年、2000年)就開始布局,發(fā)牌早不見得是好事,歐洲光牌照費(fèi)僅德國(guó)、英國(guó)、法國(guó)三個(gè)國(guó)家政府就收了1200億美金,政府等于提前收稅了,最后買單的還是老百姓,運(yùn)營(yíng)商卻弄得很慘。這兩年3G的商業(yè)化才真正起來。中國(guó)也曾經(jīng)有過各種意見,3G是早發(fā)還是晚發(fā)的,我覺得這兩年發(fā)牌照是一個(gè)比較好的時(shí)期,無論是商業(yè)化的成熟度還是老百姓可以承擔(dān)的成本、業(yè)務(wù)的豐富性,3G的需求才真正起來,建網(wǎng)成本也大大降低。整體上看,我覺得政府在重組和3G幾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的布置上是合理的,中國(guó)這么大國(guó)家,市場(chǎng)完全是可以容納三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的。
《21世紀(jì)》:對(duì)TD的爭(zhēng)議一直是存在的,過去有人認(rèn)為TD綁架了中國(guó)的3G進(jìn)程,即便到今天TD真正上馬后,人們對(duì)它的前景依舊是擔(dān)憂的,您如何看這些不同角度發(fā)出的不同的聲音?
侯為貴:國(guó)家為什么要扶持TD-SCDMA?主要是因?yàn)橹袊?guó)這么多年真正在世界形成全球化標(biāo)準(zhǔn)的產(chǎn)業(yè)很少。這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應(yīng)該說對(duì)國(guó)家整體的技術(shù)、能力的一個(gè)檢驗(yàn),特別是在中國(guó)科技階層的影響力很大,如果這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名存實(shí)亡的話,對(duì)中國(guó)的自主創(chuàng)新,對(duì)技術(shù)人才來講,信心和情緒都會(huì)受到打擊!有人講這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沒有什么生命力,其實(shí)中國(guó)這么大的市場(chǎng),這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完全是能夠成長(zhǎng)起來的,它是有足夠市場(chǎng)支撐的。從商業(yè)角度看,三大3G標(biāo)準(zhǔn)共用技術(shù)就占了70%,所以有很多技術(shù)都是通用的,剩下的30%,投入也就這么大,也不是什么東西都需要從頭做起,只要把產(chǎn)業(yè)鏈、整體布局做好,市場(chǎng)的推動(dòng)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國(guó)家下決心讓一個(gè)運(yùn)營(yíng)商去做TD,這個(gè)決策是有分量的,應(yīng)該把TD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當(dāng)成是一個(gè)國(guó)際標(biāo)準(zhǔn)來看,它將來還要不斷地發(fā)展,現(xiàn)在的技術(shù)淘汰很快,TD也會(huì)還向后演進(jìn)。從全球的角度來講,每一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要有一定規(guī)模的市場(chǎng)支撐才能夠生存發(fā)展。中國(guó)這么大的市場(chǎng)支撐著三大標(biāo)準(zhǔn)是沒有問題的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我們理解是三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都上是一種博弈的結(jié)果,這種結(jié)果會(huì)不會(huì)給企業(yè)帶來困惑?比如說,中興要在三大標(biāo)準(zhǔn)上全線出擊,資金投入上是不是有壓力?
侯為貴:任何一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也好、技術(shù)也好,進(jìn)入市場(chǎng)都有國(guó)家利益與各個(gè)利益集團(tuán)之間的博弈。在這個(gè)博弈過程中,中國(guó)一定要考慮國(guó)家利益,同時(shí)也要考慮其他的國(guó)家利益,中國(guó)是經(jīng)濟(jì)大國(guó),大家互惠互利取得平衡,這是必要的。
這個(gè)局面下,對(duì)中興會(huì)構(gòu)成一個(gè)問題,有人會(huì)懷疑中興產(chǎn)品門類比較全,資源分配是不是會(huì)很分散?其實(shí)我們現(xiàn)在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跟我們面臨的處境是一樣的,他也是各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都得做,為什么呢?因?yàn)榭蛻艟褪切枰粋€(gè)完整的解決方案,如果你有些產(chǎn)品沒有的話,你就得買別人的產(chǎn)品組合成一個(gè)方案給客戶,那樣成本更高;第二,很多技術(shù)公用平臺(tái)占到70%到80%,在這個(gè)基礎(chǔ)上,把公用基礎(chǔ)平臺(tái)做好,在這上面開發(fā)各種應(yīng)用產(chǎn)品不會(huì)投入很大的資源,這筆帳算下來應(yīng)該還是產(chǎn)出大于投入。所以說多產(chǎn)品線對(duì)我們并不會(huì)構(gòu)成壓力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最近兩年全球電信設(shè)備商正在經(jīng)歷新一輪的洗牌,在去年的銷售規(guī)模排名中,中興已經(jīng)進(jìn)入全球第八位,但是成本競(jìng)賽和非常規(guī)手段和惡性競(jìng)爭(zhēng)也在加劇,您如何看待其中的機(jī)會(huì)與挑戰(zhàn)?
侯為貴:現(xiàn)在的趨勢(shì)很明顯,西方公司都在走下坡路,包括合并的企業(yè)都出現(xiàn)了虧損,阿朗(阿爾卡特-朗訊)也好,諾西(諾基亞-西門子)也好,他們的合并是不得已的。包括北電在內(nèi)也在迅速下滑,現(xiàn)在股價(jià)是1塊多美元[HW1]以下。從宏觀來看,確實(shí)我們有很多機(jī)會(huì),但是真正要把市場(chǎng),特別是歐美高端市場(chǎng)拿到手,是非常難的。因?yàn)楦鱾€(gè)國(guó)家所謂的保護(hù)壁壘還是很高,我們屬于西方世界對(duì)中國(guó)要進(jìn)行封鎖的領(lǐng)域,歐盟對(duì)我們進(jìn)入設(shè)置了很多障礙,它要保護(hù)阿爾卡特、愛立信、諾基亞這些公司;北美市場(chǎng)呢?歐美之間雖然也有互相打仗的,但是讓中國(guó)公司進(jìn)入,還是讓歐洲公司進(jìn)入,也是有不同待遇的。另外歐美企業(yè)客戶關(guān)系是長(zhǎng)期固定的,要取得高端客戶的認(rèn)可也需要很長(zhǎng)時(shí)間才能慢慢轉(zhuǎn)變他們的觀念,一般一個(gè)產(chǎn)品進(jìn)入之前要經(jīng)過三年不斷的測(cè)試,花的時(shí)間越長(zhǎng),投入就越大,反過來如果前期不投入,那就永遠(yuǎn)進(jìn)不去。所以我們一直都在量力而行地投入,急于求成不行。
當(dāng)然我們每年都要增長(zhǎng),我們現(xiàn)在歐美市場(chǎng)每年增長(zhǎng)超過50%,我認(rèn)為這個(gè)步子還是可以的。
《21世紀(jì)》:請(qǐng)?jiān)试S我們開一個(gè)玩笑,有人談到“中華”合并的設(shè)想,這個(gè)可行性為零吧?
侯為貴:我看這個(gè)不大可能,兩家的各種差距太大了。
《21世紀(jì)》:但像西門子和諾基亞差距也很大,都有非常強(qiáng)勢(shì)的文化,但是為了生存也得要合并。
侯為貴:中國(guó)國(guó)內(nèi)企業(yè)的購(gòu)并時(shí)代,還遠(yuǎn)遠(yuǎn)達(dá)不到西方那樣的環(huán)境和條件,這可能也是市場(chǎng)化程度不斷深化的原因。歐美企業(yè)目前的發(fā)展最主要是靠購(gòu)并來達(dá)成,自身發(fā)展是第二位的。而我們?nèi)允强孔陨頋L動(dòng)發(fā)展為主,購(gòu)并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,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購(gòu)并,這(中國(guó)和西方)不太一樣,這里面有很多因素。
《21世紀(jì)》:從全球市場(chǎng)環(huán)境來看,別人在衰退,我們?cè)谶M(jìn)步,市場(chǎng)格局的確對(duì)中興、華為這樣的企業(yè)存在很多機(jī)會(huì)。但是現(xiàn)在整個(gè)全球的經(jīng)濟(jì)環(huán)境也面臨著一個(gè)很大的挑戰(zhàn)。你們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華為總裁任正非今年提出了一個(gè)“信息產(chǎn)品過剩”的論斷,并且他認(rèn)為“價(jià)格戰(zhàn)”是必然到來的。中興如何能夠讓投資者理解公司長(zhǎng)期戰(zhàn)略和短期利益之間的關(guān)系?
侯為貴:中興上市歷來都遇到這樣的問題,就是所謂的發(fā)展和利潤(rùn)之間的矛盾。發(fā)展就是你的市場(chǎng)占有率要擴(kuò)大,但同時(shí)還要確保足夠利潤(rùn),我們總是要不斷地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點(diǎn),從而給企業(yè)創(chuàng)造一個(gè)穩(wěn)健的、長(zhǎng)壽的機(jī)會(huì)。我們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太快,量力而行,但如果為了要節(jié)省成本、增加利潤(rùn),市場(chǎng)上有很多應(yīng)該拿的市場(chǎng)機(jī)會(huì)不去拿,企業(yè)就要走向另外一個(gè)極端,所以說這兩個(gè)都要尋求平衡,不可能所有機(jī)會(huì)都能拿到,就這么簡(jiǎn)單。投資者還是希望有較高的利潤(rùn),我們也希望,但是不能過高,因?yàn)槲覀兊难邪l(fā)投入還很大,在保證一個(gè)基本的利潤(rùn)目標(biāo)前提下,我們還得要有進(jìn)取心去擴(kuò)大市場(chǎng)占有率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最近幾年看中國(guó)是一個(gè)往上走的態(tài)勢(shì),中國(guó)的企業(yè)也是一個(gè)往上走的趨勢(shì)。您剛才也講到國(guó)家間博弈和跨國(guó)公司的博弈,有西方媒體會(huì)說,中興和華為實(shí)際上是利用中國(guó)的外交實(shí)力或者是外交博弈去獲取市場(chǎng),您怎么看待這個(gè)問題?
侯為貴:從外交關(guān)系來看,我們市場(chǎng)做得好的國(guó)家往往也是國(guó)家關(guān)系比較好的,這是一定的。整個(gè)中國(guó)在非洲的形象比較好,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做非洲市場(chǎng);東南亞市場(chǎng)過去不太好,這幾年“東盟”關(guān)系變化很大,我們東南亞的市場(chǎng)就起來了,包括印度、印尼規(guī)模就很大,中興一年在印度有7到8億美金,印尼今年超過5億美金,這些市場(chǎng)都跟國(guó)家關(guān)系的改善有密切關(guān)系。
創(chuàng)新戰(zhàn)略的國(guó)家路徑與企業(yè)路徑
中國(guó)3G標(biāo)準(zhǔn)——TD-SCDMA的上馬,打破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(guó)在重大高技術(shù)領(lǐng)域商業(yè)化成功的零紀(jì)錄。我們?cè)?jīng)在航天、雜交水稻、核子物理等科技創(chuàng)新領(lǐng)域獲得過“舉全國(guó)之力”的成功,但其體制色彩濃厚,欠缺在技術(shù)與商業(yè)的結(jié)合上的一套成熟體系,TD或許是一次有力的嘗試。中國(guó)在國(guó)家資源與企業(yè)路徑之間,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可以商業(yè)化、市場(chǎng)化,并成功參與全球競(jìng)爭(zhēng)的協(xié)同機(jī)制?中國(guó)的人才體系、政府財(cái)政支持等軟實(shí)力的構(gòu)建應(yīng)該如何增強(qiáng)?改革開放30年建立起來存量資源——龐大的經(jīng)濟(jì)規(guī)模、產(chǎn)業(yè)配套能力,人才儲(chǔ)備——應(yīng)當(dāng)如何盤活?
類似的追問,應(yīng)該不厭其煩。
《21世紀(jì)》:從工程師到企業(yè)經(jīng)理人,到一個(gè)跨國(guó)公司的領(lǐng)導(dǎo)者,從您的視野來看,中國(guó)科技創(chuàng)新戰(zhàn)略這幾年走得怎么樣,您覺得有沒有一些問題,中國(guó)要建構(gòu)未來的自主創(chuàng)新戰(zhàn)略要解決哪些體制問題?
侯為貴:國(guó)家創(chuàng)新體系這些年也是在不斷地改進(jìn),過去像“863”計(jì)劃都是以高校為主,現(xiàn)在是以企業(yè)為主,雖然很多人有對(duì)此有看法,但我認(rèn)為這種轉(zhuǎn)向是對(duì)的。在科技領(lǐng)域做得比較成功的歐美國(guó)家,它的創(chuàng)新主體都是以企業(yè)為主,如果由院校派為主體,最后對(duì)生產(chǎn)力的推動(dòng)肯定是大打折扣的。當(dāng)然國(guó)家在財(cái)政制度上對(duì)科技產(chǎn)業(yè)的投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,國(guó)家購(gòu)買國(guó)外金融資產(chǎn)的同時(shí),決定層應(yīng)該在實(shí)業(yè)投資上多作考慮。
《21世紀(jì)》:中央從世紀(jì)初就在講“創(chuàng)新城市”,深圳的經(jīng)驗(yàn)是R&D投入90%以上來自企業(yè),這個(gè)的確顛覆了過去以院校為主體的創(chuàng)新模式,但是最近深圳也在反思,按照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的經(jīng)驗(yàn),R&D投入政府和企業(yè)的投入是各占50%,因?yàn)槠髽I(yè)研發(fā)會(huì)天然地接近市場(chǎng)和商業(yè)化,而基礎(chǔ)研發(fā)和創(chuàng)新以及人才的培養(yǎng)依舊要依靠國(guó)家投入,深圳在政府投入上的缺位實(shí)際上這幾年已經(jīng)動(dòng)搖到深圳的人才環(huán)境、科技創(chuàng)新的軟實(shí)力。您如何看政府在科技創(chuàng)新上承擔(dān)的角色?
侯為貴:從高科技成果轉(zhuǎn)化的主要?jiǎng)恿砜矗瑖?guó)家應(yīng)該主要投入一些基礎(chǔ)性的,像科學(xué)院、中科院,應(yīng)該是國(guó)家全面投入。這個(gè)投入在整個(gè)自主創(chuàng)新投入里面比重不應(yīng)太大,其他一些應(yīng)用型創(chuàng)新技術(shù)還應(yīng)該是投入的大頭,這部分應(yīng)該是以企業(yè)為主體,國(guó)家可以建立起基金、創(chuàng)投參與支持,這是合理的。但應(yīng)用型創(chuàng)新不能以國(guó)家的資金為主,如果那樣的話最后國(guó)家體制會(huì)出問題,誰來對(duì)這么一大筆錢負(fù)責(zé)?
美國(guó)在戰(zhàn)斗機(jī)等軍事項(xiàng)目上是國(guó)家對(duì)企業(yè)進(jìn)行投入的,涉及到幾百家企業(yè),但這是一種國(guó)家主權(quán)PE的方式,產(chǎn)權(quán)是國(guó)家的,最后飛機(jī)賣到很多國(guó)家,收回的錢也仍然是國(guó)家的,這有一套完整的商業(yè)運(yùn)作方式。中國(guó)還沒有這套東西,我們的政府現(xiàn)在缺少一套組織機(jī)制和流程,沒有這套商業(yè)化的體制。
國(guó)家的機(jī)制怎么樣進(jìn)一步地變革,成為中國(guó)科技創(chuàng)新的一個(gè)動(dòng)力?國(guó)家這幾年在稅收政策上對(duì)軟件業(yè),以及科技人員有一些稅收返還,這些政策形成一定的推動(dòng)力,但目前中國(guó)包括財(cái)稅在內(nèi)的政策改進(jìn)空間還很大。從戰(zhàn)略上看,國(guó)家應(yīng)該站的高度更高一些,哪些行業(yè)應(yīng)該有更多的重點(diǎn)投入,國(guó)家財(cái)政如何投入科技實(shí)業(yè)?我認(rèn)為中國(guó)這方面還是欠缺的。其實(shí)要做起來也不難,你就把美國(guó)這些大的科技項(xiàng)目是怎么做的出來的,好好深入地研究一下,具體如何與我們的國(guó)情相結(jié)合,就能夠把這個(gè)事情慢慢做起來,我認(rèn)為他們現(xiàn)在對(duì)歐美創(chuàng)新模式的研究還是太少、太淺。
《21世紀(jì)》:您是做半導(dǎo)體IC出身的,中國(guó)在IC、軟件等產(chǎn)業(yè)上一直有某種情結(jié),比如總是有人喜歡拿印度的軟件業(yè)與中國(guó)來比,這其實(shí)反映了中國(guó)在高科技領(lǐng)域的失落感。您對(duì)中國(guó)這幾年IC以及軟件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怎么看?
侯為貴:我覺得我們的軟件跟印度是各有所長(zhǎng),我接觸了很多印度技術(shù)上的領(lǐng)導(dǎo)者,他們還很羨慕我們,認(rèn)為我們有自己的系統(tǒng)和自主品牌,他們的軟件業(yè)等于是加工,跟來料加工是一樣的。印度的優(yōu)勢(shì)就是把加工做得非常好、非常大,我們的優(yōu)勢(shì)就是能夠成為一個(gè)系統(tǒng)產(chǎn)品,成為一個(gè)品牌,能夠自由發(fā)展。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,并不是很了解軟件內(nèi)在的過程,其實(shí)中國(guó)人軟件、硬件都是可以的,我們現(xiàn)在的軟件是一種系統(tǒng)軟件和產(chǎn)品相結(jié)合的,嵌入式的為主,中興的軟件技術(shù)人員占了70%,研發(fā)人員當(dāng)中30%做硬件,70%做軟件,實(shí)際上是以軟件為主的企業(yè)。
我做IC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,我覺得我們IC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現(xiàn)在走的路子基本上是引進(jìn)生產(chǎn)線制造,但是對(duì)于設(shè)計(jì)這一塊我覺得政策支持還不是很充分。中國(guó)應(yīng)該把重點(diǎn)放在IC設(shè)計(jì)上,生產(chǎn)線你花錢0.65微米的都能買到,再引進(jìn)一些管理人員做好生產(chǎn)和成本管理就可以了,現(xiàn)在的貿(mào)易保護(hù)在這方面障礙越來越少了。但是IC設(shè)計(jì)就不一樣,設(shè)計(jì)的技術(shù)涉及面非常廣,小企業(yè)能做,大企業(yè)也能做,對(duì)提升科技競(jìng)爭(zhēng)力非常重要,這方面國(guó)家應(yīng)該更多地關(guān)注,應(yīng)該成為一個(gè)著眼點(diǎn)。
新聞來源:南方報(bào)業(yè)傳媒集團(tuán)-21世紀(jì)經(jīng)濟(jì)報(bào)道
相關(guān)文章